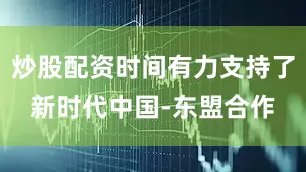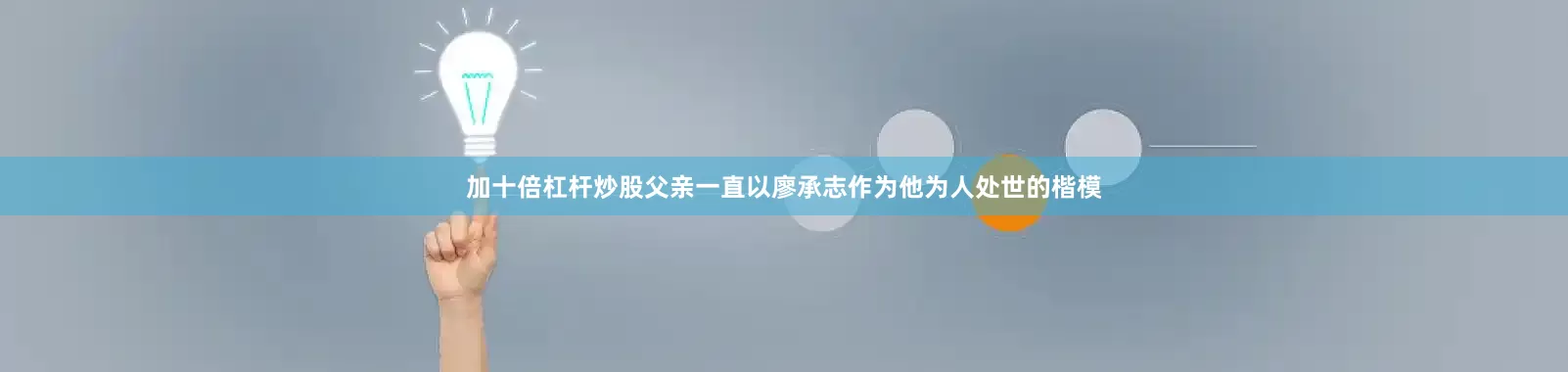
于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内,宋庆龄致邓广殷的遗嘱已被精心雕刻成牌匾,安详地陈列于馆中。然而,多数来访者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更遑论知晓这份曾深藏瑞士银行保险箱之内的遗嘱背后的曲折历程。
在宋庆龄的遗愿中,她将北京与上海两座住所内的全部藏书,视为回馈,无偿赠予邓广殷。在这些私人财产中,这部分藏书无疑是最为珍贵、价值最高的。宋庆龄一生钟爱阅读,众多友人慷慨馈赠,她也乐此不疲地收藏。这些藏书伴随宋庆龄度过了漫长岁月,其中不乏诸多今已绝版的国内外经典。
仅在上海的故居,藏书就达到了4900余册,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十二大门类。这些书籍的语言除了中文,还包括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朝鲜文、拉丁文等十七种文字。其中,许多书籍的出版年代可追溯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古老的文献是1811年发行的文学著作——英文版的《弗罗丽达的故事》。
邓广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宋庆龄会将自己宝贵的藏书毫无保留地赠予他?
非偶然获赠全部藏书。
邓广殷,出身名门望族,现任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曾担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的委员,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同时也是我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的子女。

▲邓文钊一家的温馨合影映入眼帘,前排伉俪情深,分别是邓文钊及其夫人,后排则站立着邓广殷及其夫人。
邓家与廖家素来有亲缘之谊。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女士,乃是何香凝女士的侄女。邓文钊先生在早年求学时期,便曾与避难于香港的廖梦醒女士和廖承志先生姐弟共同度过了数月时光。他对这姐弟俩,年龄相仿却传奇色彩十足,心怀深深的敬佩。尤其对表兄廖承志,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父亲一直以廖承志作为他为人处世的楷模,甚至要求他必须就读于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频繁邀请友人至邓文钊府邸聚会,共商组建一个机构,旨在为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持续不断的物资与医疗援助。彼时,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一职。他以满腔爱国热忱,积极协助廖承志在香港展开工作。廖承志遂将邓文钊引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共同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即今日的中国福利会)。
宋庆龄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则担任中央委员兼司库,自此成为宋庆龄的至亲好友。为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囊相助,并将自家的客厅与游泳棚提供给宋庆龄接待贵宾之用。为解决保盟的车辆和交通运输问题,他还将自己的两个大型仓库无偿提供给保盟使用,专用于存放准备转运至抗日根据地的救援物资。海外的大宗捐款与救援物资均由他亲自接收,并转送至抗日后方和延安。凭借其富商身份,他出面为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并成为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然而,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不幸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深厚情谊亦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自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的状况长期存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与药品。邓家父子便利用香港的渠道,持续不断地为宋庆龄输送所需物资。宋庆龄曾多次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却难以回报,她赞誉邓家父子始终履行着“司库”的使命。
宋庆龄生前视邓广殷如同己出,自1971年起便开始给他写信。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即1971年至1980年,她总共向邓广殷寄出了189封亲笔信。在这些信件中,她总是亲切地以“BB”称呼他。

▲1974年,邓广殷(位于中间)与宋庆龄共同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密存瑞士银行遗嘱
亲爱的广殷:
我急忙写下这些文字,旨在告知您,我们已接到消息,本月月底前将有一次约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京。您不难想象,人们此刻普遍感到紧张。我的上海朋友们敦促我返回上海的住所,但如此一来,恐怕会加剧当地民众的恐慌情绪。因此,我选择留在此处,无论未来将面临何种情况。
我已草拟完毕遗嘱,此外,我还想附加一份仅由你负责保管的私人文书。
我从邓广殷的女儿邓勤那里得知,她已顺利通过考试,心中喜悦不已。我计划在期中考试期间前往苏黎士游览一番。
愿您与家人康健无恙,期许您的哮喘病症已然康复。
问候你和家人。
诚挚的伯婆
“此遗嘱于1975年2月18日订立。若不幸发生意外,我决定将位于北京与上海淮海路1843号之家的全部藏书赠予恩斯特·邓,以此纪念他对我所施予的种种善举。宋庆龄谨书。”

▲宋庆龄遗嘱
邓广殷在接到宋庆龄寄来的遗嘱后,深感此事非同小可,遂决定秘而不宣,并加以妥善保管。恰逢其时,他的女儿邓勤正在瑞士洛桑的旅游管理学院深造,而他亦计划前往瑞士探望女儿。于是,他迅速携带遗嘱前往瑞士,将其存放在当地银行的保险柜内。
捐赠全部藏书给国家
在1981年6月,由邓颖超同志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中明确指出:邓广殷同志已作出声明,拒绝接受所赠书籍,并将之上交国家处理。
又是怎么回事?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香港分社新华社的紧急召唤及机票,要求他立即前往北京。抵达北京后,他方得知宋庆龄病情危急。作为香港唯一被邀请的宾客,邓广殷得以在北京陪伴宋庆龄。他每日前往探望,直至5月29日宋庆龄离世。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守灵和悼念等仪式。
宋庆龄曾叮嘱他不要泄露遗嘱之事,因此,直到悼念活动落幕,他未曾提及遗嘱。随着国外亲友陆续离开,邓广殷也准备返回香港。就在此时,廖承志劝他暂留,多住几日。邓广殷便每日到廖承志家中品茗谈天。直到邓先生的母亲焦急万分,写信向北京请求让邓广殷归家。于是,某日,廖承志将邓广殷请至家中,关上房门,询问他是否知晓宋庆龄的遗嘱。
显而易见,廖承志未曾目睹宋庆龄亲笔致邓广殷的遗嘱。他所见到者,仅为宋庆龄留下的副本,其中包含了关于她遗产处理的个人意见。邓广殷对此回应,确有遗嘱,但并未随身携带,亦未计划出示。
廖承志询邓广殷如何行动。
邓广殷未料及此事,随口应道:“不妨捐赠给国家吧?”
廖承志立刻回应:“很好,请将这层意思详细记录下来。准备一份捐赠报告吧。”
邓广殷坦言自己笔触生疏,对格式亦不熟悉,遂恳请廖承志协助代笔。
廖承志动作迅速地抓起笔和纸,现场草拟了一份文稿,既快又简洁。他随即指示邓广殷照着这份文稿一字不漏地复写,并要求其签名确认。
紧接着,廖承志迅速将邓广殷亲笔签署的捐赠报告收好,告知邓广殷可以启程返回香港。
我向邓先生咨询,是否需要保留一份草稿或捐赠报告副本?
他说,当时一切发生得极为迅速,他心中一片混沌,并未深思,只记得那些草稿、捐赠报告等,都被廖承志取走,毫无所剩。他深知,宋庆龄的藏书众多,分别存放于北京与上海,根本无法携带,更无法运回香港的家中。他相信,将这些藏书捐给国家,才是最为妥善的选择。即便时至今日,他仍不认为自己将宋庆龄所赠藏书捐出,有何等伟大之处,也未曾向国家或相关部门提出任何要求,甚至未曾见过宋庆龄赠予他的全部书籍。而那场捐赠仪式,则是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发起,并坚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她认为,若不如此,对邓广殷来说,实在是不公平至极。

▲宋庆龄藏书
提及邓先生在得知宋庆龄所留遗嘱时的内心感受,他动情地赞誉宋庆龄为一位令人敬仰的伟大人物。回忆1975年收到宋庆龄遗嘱信件的那刻,他既紧张又深受触动。这份震撼并非源于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对她面临危难时仍保持镇定自若、勇敢无畏的态度,以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精神所敬佩。
在地震即将降临之际,宋庆龄选择与民众并肩作战。她明知危险,却毫不畏惧,从容安排后事,展现了她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体现了她冷静果敢的意志。邓广殷对此深感钦佩,记忆犹新。他强调,在关键时刻,宋庆龄所展现的正是她作为伟大人物所拥有的高尚品质。
至于宋庆龄所留下的那封遗嘱,邓广殷深感其中不仅蕴含着宋庆龄对他的深厚情谊,更映射出她一贯的品格——始终铭记他人曾给予她的援助。她以真挚的感激之情,向所有曾伸出援手、为她付出哪怕微薄之力的人,表达了肺腑的谢意。
上海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